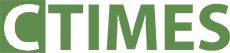南部小鎮,相對於橫衝直撞的年輕,顯得太過輕薄短小。死板的柏油路,一棵棵行道樹乾涸地將脖子伸進天空,透氣。沒有雲的藍天氣,站在騎樓外的人行道上,讓視線穿過紅綠燈、十字路口、窄巷、車流、人群、高樓,把頭抬高一些,就可以看見天空刺眼的陽光。
 |
| /news/2009/08/04/0945422245.jpg |
午後的長街,朋友站在身後,問我看見了什麼?我苦悶起來。遠方的摩天大樓一幢幢不斷攀高,原來,我看見了迷戀北方城市的17歲,我看見了旅行的起點。
遲滯的夏日,鋪陳在世界地圖上的許多地名,都是無法成行的渴望。我花去大把時間看著遠方,發呆,哪兒都沒去成。常常不太說話,沈默著,把心事都投射在遠方地平線上,好像就會有人懂了。有那麼一次,我真的趁著沒人注意,翻越過圍困這小鎮的矮牆,旅行去了。我跑過夏日曝曬的鄉間小路,稻穀攤曬在地上,蒸出飽滿的氣息。沒有人煙的午後,沒有風,三合院裡晾曬的衣物不動如山。我繼續奔跑,然後,聽見背後傳來城市裡此起彼落的車流聲。我回頭,擁擠人潮從我身邊快步通過,喧囂、熱鬧。這是大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,而我路經。
直到我搭上高鐵列車,低空飛越陌生的窗景,我才確定自己已經離開小鎮了。降落,在台北這一窪盆地之上。
幾分鐘前,我還在陽光的手掌撫弄之中,看著列車窗外映射著光芒的嘉南平原。我總以為,在平原延伸的遠方,可以看見那個我一直急欲離開的小鎮。我輕盈,飛揚如一片不解世事的羽毛,一轉眼,就跨越了17歲,跨越了起點。
我帶著微笑,從窗口沿途辨認長長的地平線。那被無限展延的年少時光。是這樣的,一旦離開,我就不會再回頭。回頭,只會看見舊地。我就是這樣,以一個堅決的手勢,將自己從小鎮推進城市。大城市滋養、壯碩了乾涸的年輕,當我邂逅了希望與失望並列的城市,我開始習慣嫻熟地包裝自己。
列車進站,車廂內的燈光全部暗去,我才確定自己真正離開了。因為那樣的確定,突然,我苦悶起來。我在不為人知的悲傷中,自虐地咀嚼一齣自導自演的獨角戲。來到著迷的北方,才知道,只有那執迷不悟的17歲,是一旦跨出,就再也無法返回的禁區。既使有了再快的通訊科技,也不能將我帶回到起點。
當我望著列車緩緩駛進台北,不禁想問,是不是,其實我一直在飛行,根本沒有落地?